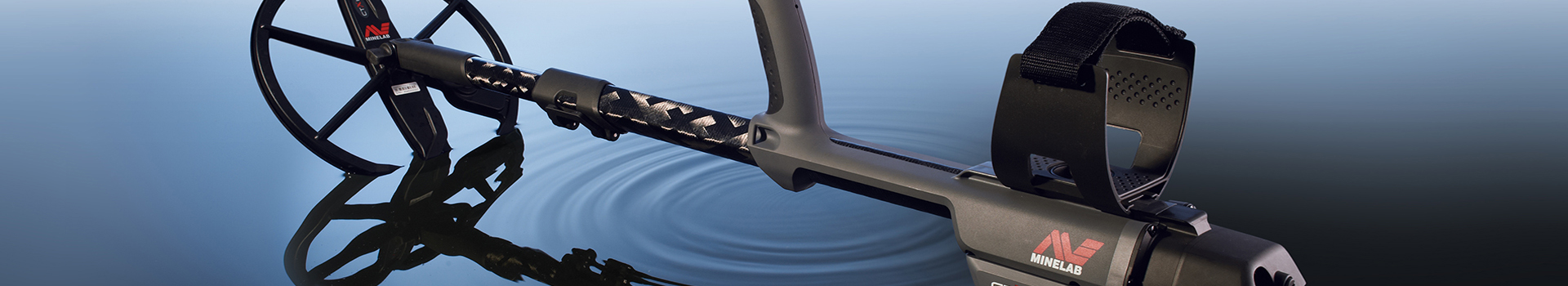中国对香具的利用在夏商周三代就已开始了,或者说香具文化已经形成了,——因为香的使用已分出了供香、礼香、药香体系与系列,而且香文化已融入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。从现有的资料研判,夏代行祭的香具,已知有彝鼎之属。商代的盛香用具已有陶器和部分青铜礼器了。周代祭祀用的青铜香具和陶香具已经很完备了。
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,古代文献记载既少,又多模糊不清。有关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,目前还在继续探索中。但是我们已经知道,夏代社祀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,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代社祀的基本功能。《夏书·胤征》《尚书·尧典》都记载有夏代祭祀日神之礼。从现有的资料研判,行祭的香具,仅知有彝鼎之属。辟秽清洁之香具,目前尚不得而知。
宋代丁谓著《天香传》中云:“香之为用,从上古矣。所以奉神明,可以达蠲洁。”说的是用香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期,用来供奉神明,亦可达到辟秽清洁的目的。丁谓还引《三皇宝斋》赞美“古圣钦崇之至厚,所以备物实妙之无极”时说,香珠法制香工具“缄以银器”。宋代高承撰《事物纪原》,专记事物原始之属。其中曰:“黄帝内传有博山炉,盖王母遗帝者,盖其名起于此尔,汉晋以来盛用于此。”丁谓和高承的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得到证实,但是,宋人的这个上古之人用香具的观点是存在的。
唐代孔颖达撰《尚书注疏》,其中谈道:“我闻曰:至治馨香,感于神明。黍稷非馨,明徳惟馨。(传:所闻上古圣贤之言,政治之至者,芬芳馨气动于神明,所谓芬芳非黍稷之气,乃明德之馨,励之以德也。)尔尚式时,周公之猷训,惟日孜孜,无敢逸豫。(传:汝庶几用,是周公之道教殷民。惟当日孜孜勤行之,无敢自宽暇逸豫。”)《尚书》是儒家五经之一,在香文化的领域里,它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书籍。因为它标示出香文化之于政治功能的最重要的一点——明德。
关于烧香与祭祀、拜佛敬道,北齐魏收撰写的《魏书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汉武元狩中,遣霍去病讨匈奴,至皋兰,过居延,斩首大获。昆邪王杀休屠王,将其众五万来降。获其金人,帝以为大神,列于甘泉宫。金人率长丈余,不祭祀,但烧香礼拜而已。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”自周代以来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汉武帝时缴获“金人率长丈余,不祭祀,但烧香礼拜而已”,可见外来的和尚,在汉武帝时并不吃香。
史前文明中最初的香具主要用于祭祀、驱瘟避疫,香料有三牲、鬯酒、烤肉和各种花草类香等。对史前的香具,尽管学界有争议,但是马家浜文化香熏炉的发现,说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有香具的出现,在学界还是得到认可的。
商代用香延续夏代,辟秽清洁之香具,目前亦尚不得而知。祭祀香具有所发展。从商代起,我国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。我国商代的青铜器具,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,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。商代的青铜礼器如鼎、鬲等多用于盛放牺牲类香材和酒类香材,用于祭祀。
“周人尊礼”,因此礼法完备,香材、香具都有完善。《礼记》《周礼》等典籍对陶匏、陶豆(登)、圭、璋、瓒等祭祀香具多都有记载。这是中原地区可考的最早的陶瓷类香具了。
《尚书·舜典》载:“岁二月,东巡守,至于岱宗,柴。望秩于山川,肆觐东后。协时月正日,同律度量衡。修五礼、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贽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柴”就是“柴祭”,是后世“香祭”的滥觞。《尚书·舜典》又载:“肇十有二州,封十有二山,濬川。”说的是当时柴祭的形式是封土为坛举行祭祀。那么承香之具就是土坛了。
除了上述说的香具用于祭祀外,在治理国政的教化中,熏香炉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。东晋方士王嘉曾说:黄帝“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,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,燃沉榆之香”。可见,中国最早的治理国家的最高领导集团,其统一思想是在香烟缭绕的环境下完成的。
《礼记·郊特牲》载:“天子适四方,先柴。郊之祭也,迎长日之至也,大报天而主日也。兆于南郊,就阳位也。扫地而祭,于其质也。器用陶匏,以象天地之性也。”宋代著名学者林之奇撰《尚书全解》中云:“敬念祭祀之事,尝考之诗如曰:昂盛于豆,于豆于登,其香始升,上帝居歆,胡臭亶时。”这些仪式所用之器,即为“盛香”之具。“于豆于登”,即香具。语本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:“于豆于登。”毛传:“木曰豆,瓦曰登。豆荐葅醢也,登盛大羹也。”孔颖达等奉敕撰《礼记正义》云:“其祭天之器,则用陶匏。陶,瓦器,以荐菹醢之属,故《诗·生民》之篇述后稷郊天云‘于豆于登’,注云:‘木曰豆,瓦曰登。’是用荐物也。匏酌献酒,故《诗·大雅》美公刘云:‘酌之用匏。’注云:‘俭以质。’祭天尚质,故酌亦用匏爲尊。皇氏云‘祭天用宗庙牺尊’,皇氏又云‘祭天既用牺尊,其陶匏者,是盛牲牢之器’。今案陶匏所用,如上所陈。”《尚书通考·卷三》亦云:“扫地而祭,于其质也。器用陶匏,以象天地之性也。”孔颖达疏:“陶谓瓦器,谓酒尊及豆簋之属,故《周礼》旊人为簋。匏谓酒爵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