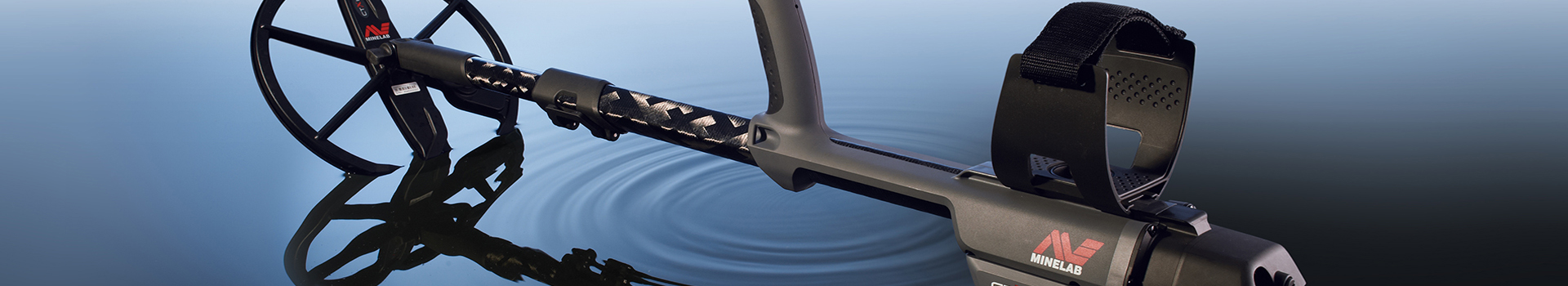作为汉学大家,乔迅在学术范式上的突破之处在于,他擅长将实在的物或人“符号化”。在他眼中,世间万物的表象之下皆遮蔽着隐喻的意义空间。在早年著作《石涛: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》中,乔迅就检视了石涛画作所隐含的精神性———石涛作品中郁郁葱葱的蔬菜花卉,被乔迅解读为象征兴奋的身体语言。《魅感的表面》接续了上书的路径,引导我们审视的装饰,不仅停留在华美的层面。他强调,装饰品是人体器官和感官的延伸,当人与装饰品发生互动,自然能体会到仿佛与自己对话和嬉戏般的亲切和愉悦。装饰品也隐喻和延伸着人的身体,比如,花瓶的流线型外观让人联想到妙龄女子的婀娜体型;高足杯的耳柄是对饮者双手的邀请……二维和三维的装饰品表域(surfacescape)吸引着人的眼睛、双手、皮肤和五脏六腑,将人的反应导向于满足的心理状态,同时又通过有意识的修辞,营造着隐喻空间,并生产意义。对于表域的迷恋,说明人视这些表域为满载着情感的同类,因此,“通感”“移情”等特异的审美体验才得以实现。
所谓“玩好之物”,指的是供人赏玩,被人喜欢,引起人的感官愉悦的器物。在艺术史、美术史或者文化史上,多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客观存在而进行描述和研究。但在新近出版的《魅感的表面》一书中,美国艺术史学者乔迅试图以欣赏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,通过探讨器物的“表面美”,一窥人们从玩好之物中获得愉悦时,到底与其发生了怎样的互动?
单个物品的表域不仅形成了微观世界,还在建筑内外形成了形势布局,乔迅将其称为“物境”(objectscape)。《金瓶梅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浮生六记》等明清小说中皆有大量篇幅对此展开描绘———不同的器物带着不同的气息,但摆在一起,就像博物馆,构成了丰富的形势布局,比如,“清清独坐,只见满架诗书,笔山砚海”(见《警世通言·玉堂春落难逢夫》)。不同特定的“场域”(如书房、厅堂等),因为各种错落的器物,被构筑出整体性的空间“景观”。装饰的表域与周遭的环境发生着关联,并形塑和改变着室内的环境。
相较于宋人的风雅,明清的古物鉴赏已变成一场“闲”式的消费行为,对设计、布置、装饰等技巧更为侧重。随着晚明经济的繁荣、跨地区贸易的发展、作为经济重镇的城市的出现、专事流通的商业化日盛,古董市场变幻莫测,新的“时玩”风尚不断出现:“玩好之物,以古为贵。惟本朝则不然,永乐之剔红、宣德之铜、成化之窑,其价遂与古敌。”造物者们竭力在器物表面,通过装饰营造珍稀、独特、新奇、精美等充满魅感的繁茂气象,迎合、吸引收购者的“目力”。
为区别于礼仪化、宗教性和博古一类的装饰物,乔迅挑选了与居家生活空间相关的日用摆设品,不仅组接上物与人、装饰与感官之间的“暗码”,还对研究视觉性话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装饰,不仅是器物表面的工艺,给隐藏其下的形状和材料穿上华丽外衣,更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,昭示着其所有者无与伦比的优越感。在古代,士人阶层收留的器物,愈发成为彰显身份、品位的手段,就连皇室也热衷于用显见的表面化装饰来彰示权威。在此种风气的带动下,当时的皇帝、文人墨客也热衷于扮演设计者的角色,他们与手工艺者们共同努力将绝技般的技艺融入印章、瓷器、砚台等物件中,通过个性化和商业化十足的款识等外在形式来彰显品位。在此过程中,这些玩物实现着从物质性向精神性的功能转化。乔迅以当时江南、北京两个生产中心为例,详尽说明材料、工匠、资源、作坊、市场等何以造成装饰艺术的兴盛。
单色的光滑、物质性纹理、发明的纹样、图绘、铭文、虚构的表面等六种处理手法被乔迅称为“资源”,它们各擅其长,甚至可以通过压缩、分配等形式组合使用,从而与相应的表面辅车相依,最终形成表域。每一种资源都衍生出错视、戏仿等特殊的工艺,工匠借此大施才华,形成产生魅力的独特渠道。